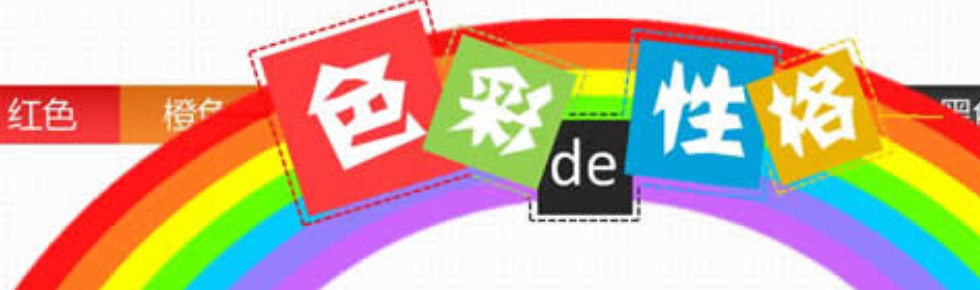撰文/冯务中
「“患失”通常会使人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一般而言,“患得”并不会使人不择手段。尽管人们在改革的过程中是有得有失的,但是人们往往更加在乎“失”而不是“得”。」
英国大文豪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的开头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奔天堂,我们都将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本来,狄更斯在这里描述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其时距今已有二百多年;但是,这段话却被很多人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的改革时期。其中缘由,发人深省。
对于改革开放,有的人认为“好得很”,有的人认为“糟得很”;有的人认为“过头了”,有的人认为“不到位”;有的人“爱之欲其生”,有的人“恨之欲其死”……中国的改革似乎成了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打造的“罗生门”:大家站在自己特定的立场上,将同一个事件说得扑朔迷离、大相径庭。对中国改革的评价似乎成了“盲人摸象”:不同的人囿于自己的能力和角度,最后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多了,不由得使人想起苏东坡那首饱含哲理的七绝《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即使“身在此山中”,也可以“一识庐山真面目”。以上关于改革的争议可以从“得”与“失”及其二者的复杂关系中得到一定的解释。
首先,改革是一个有“得”有“失”的过程。
改革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改革的进程中,人们不可能只得不失、只进不出、只赢不输、只成不败、只益不损。“稳赚不赔”此等美事只有在小说中才能出现,因为获得收益是以支付成本为前提的。世界上的道理千条万条,如果要归结为一条的话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得有失乃是生活之常态,从而也是改革的常态。
就群体而言,改革是一个有得有失的过程:一些人得到了,另一些人失去了;一些人“高富帅”了、“白富美”了、“高大上”了,另一些人“矮穷挫”、“黑穷丑”了、“低小下”了;一些人成了“官二代”、“富二代”,另一些人成了“农二代”、“贫二代”;一些人成了“温拿”,另一些人成了“卢瑟”;一些人成了“土豪”,另一些人成了“屌丝”;一些人“下海了”,另一些人“下岗了”;一些人越来越牛了,另一些人越来越怂了……
就个体而言,改革过程也是有得有失的,比如说TA(他或她)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却失去了既有的保障;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却失去了曾经的安稳;得到了更高的收入,却失去了难得的清闲;得到了“金山银山”,却失去了“青山绿水”等等。
因此,不同群体的人和不同个体的人会从自己特定的立场出发,对改革作出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评价。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中,在不同的境况下,在不同的心境下,也往往会对改革作出不尽一致甚至前后矛盾的评价。你可以至始至终让一部分人满意,你也可以短时间内让所有人满意,但是你不可能至始至终让所有人满意。做人如此,改革也是如此。
要解决“众说纷纭”这个问题,就要通过明确改革目的、优化改革方法、注重改革策略、尊重改革规律、提升改革质量、测控改革后果等方式和途径,想方设法使改革尽量成为一种“皆大欢喜”的正和博弈,而不要成为一种“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更不能成为一种“满盘皆输”的负和博弈。杜绝各种关于改革的噪音和杂音的最好办法,不是让人们“有苦难言”,而是让人们“乐在心中”。
其次,人们对“得”与“失”的感受程度不尽一致。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尼曼因其“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获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景理论”又被称为“预期理论”或“视野理论”。其要点有三: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倾向于“风险规避”,即人们在面临未到手的收益时往往会小心翼翼,宁愿坐失良机也不愿冒险一搏。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倾向于“风险偏爱”,即人们在已有之物即将失去的情况下往往会很不甘心,从而很愿意冒险一搏甚至以命相搏。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加敏感,即人们对损失与获得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致的。
对于同样一种东西,损失时的痛苦感要远远大于获得时的快乐感。比如,人们遭窃损失一万元的痛苦感往往要大于人们捡到一万元的快乐感。再比如,人们在遭受“意外之毁”时的痛苦感往往要大于人们受到“不虞之誉”时的快乐感。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成语叫做“患得患失”。这里的“患得”其实是“患不得”。此成语的涵义是:人们在未得到之前,往往担心得不到;而在得到之后,往往又担心会失去。但是,“患得”与“患失”并不是等量齐观的,“患失”往往要甚于“患得”。这就正如“患得患失”这个成语的文本渊源《论语?阳货》中所言:“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意思是说:如果担心失去,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也就是说,“患失”通常会使人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一般而言,“患得”并不会使人不择手段。
“前景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人非议改革。因为尽管人们在改革的过程中是有得有失的,但是人们往往更加在乎“失”而不是“得”。“前景理论”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改革的动力较小而阻力较大,因为改革会增加一些人“获得”的机会,但是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是风险规避的;改革也会增加一些人“失去”的机会,而人们在面临“失去”时往往是风险偏好的。
例如,人们通常不会为了获得一个“饭碗”而与人拼命,但是人们往往会因为失去一个“饭碗”而与人拼命;人们通常不会因为“上岗”而感激涕零,但是人们往往会因为“下岗”而咬牙切齿。因此,拥护改革的社会能量与阻碍改革的社会能量往往不相匹敌,除非拥护改革的人远远多于阻碍改革的人,除非主张改革的人的地位远远高于反对改革的人。
而要解决人们对“得”与“失”感觉不一致、不对称这个问题,就必须想方设法使人们在改革进程中“获得”的绝对值远远大于其“失去”的绝对值。如果人们获得的绝对值小于其失去的绝对值,人们当然会对改革产生非议;但即使人们得到的绝对值等于或相当于其失去的绝对值,人们也往往会对改革产生非议;只有当人们得到的绝对值远远大于其失去的绝对值时,改革的动力才会大于其阻力,改革才会深化下去,改革才会拥有明天。
最后,不同的比较方式也会导致对改革的争议。
人是比较的动物,人总是会选取不同的参照系进行五花八门的比较。因此,即使改革使所有人都获得了净收益,即人们所得到的绝对值远远大于其所失去的绝对值,也仍然会有人对改革产生非议。原因在于:除了将自己现在的得到与失去进行比较(简称“得失比较”)之外,人们往往还会在“得失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纵向比较”,即将自己目前的状况与自己以前的状况或者自己祖辈的状况进行比较。比较之后,如果感觉“倍儿爽”,则往往不会非议改革;而如果感觉“倍儿不爽”,则往往就会非议改革。
“纵向比较”之外,人们更倾向于进行“横向比较”,即与自己周围的人进行比较。周围的人包括自己的同学、同事、邻居、亲戚、朋友、对手、敌人等等相关人。比较的结果如果是自己优越于其他人或者优越于其他人中的多数人,则往往不会非议改革;而如果是其他人或者其他人中的多数人优越于自己,则往往就会非议改革。
很多心理学家都做过这样的实验:给测试者两个选项A和B。A代表你年收入10万元,周围的人年收入9万元;B代表你年收入20万元,周围的人年收入21万元。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A而非B,尽管B的收入要远远高于A。此实验可以说明:人们不仅追求绝对收益,而且追求相对收益。这就是人性的微妙之处。
孔老夫子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语常被人们看作是平均主义的宣言而大加鞭挞,实际上它揭示了人性共同的弱点。这种弱点是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的,因而它应该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而不应成为公共政策的改造对象。西方谚语也讲:所谓幸福的人就是自己的收入虽然很低但是比自己的邻居要高一点点的人。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写道:“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子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房子的一切需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树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喜剧演员范伟在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中有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台词:“幸福就是:我饿了,看见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虽然是戏谑之语,但却道出了“比较之中出幸福”这个真理,同时也间接地道出了“比较之中出烦恼”这个与其相反相成的真理。正是由于存在着“获得”与“失去”的“得失比较”,存在着“今天”与“昨天”的“纵向比较”,存在着“自己”与“他人”的“横向比较”,有些人才会热烈拥护改革,而另一些人却会因此而非议改革。
要解决“比较产生争议”这个问题,不能寄希望于人们放弃比较,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一张大网,人总是处于社会之网的某个节点上,作为此节点的人总是会与作为彼节点的人进行比较。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是人的天性;区别仅仅在于有的人倾向于“向上比”,有的人倾向于“向下比”;有的人喜欢比“硬实力”,有的人喜欢比“软实力”;有的人比较的方式不切实际、不尽合理;有的人的比较方式切合实际、较为合理。
所以,要解决“比较产生争议”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在一个很不公正或不很公正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会比较出嫉妒、怨气、不满、仇恨等“负情绪”,比较出怨天尤人、玩世不恭、愤懑不平、愤世嫉俗等“负心态”;而在一个相对公正的社会中,人们也会经常进行比较,但是比较的结果往往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心”、“各得其乐”、“皆大欢喜”。因此,想方设法促进社会公正,消除不合理比较的社会基础,增强合理性比较的社会基础,是解决“比较产生争议”这个问题的治本之道。除此而外,我们也应该通过适当的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合理的比较观和正确的幸福观,减少虚荣心理和攀比陋习,增强“知足常乐”的意识和“乐人之乐”的觉悟。
版权声明:本文由作者授权新华网思客独家发布,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于新华网思客。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新华网立场
关于作者冯务中:清华大学副教授
关于思客思客(sike.news.cn),新华网倾力打造的思想传播与跨界智库平台。我们在这里,与您一起,发现思想力,成就影响力。
联系我们投稿邮箱:sike
news.cn服务-
阅读本文作者的其他文章,北京市中科医院好不好初期白癜风能治愈吗